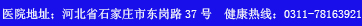李浩白关于历史小说创作的管窥之见
2023/7/13 来源:不详北京专治白癜风的正规医院 https://yyk.99.com.cn/fengtai/68389/
现当代题材的小说不好写,而历史题材的小说则更不好写。现当代题材小说创作,只要满足“准确性”、“艺术性”、“创造性”就可以了,而古代历史题材小说则要在现当代题材小说创作这几个特性上还要叠加上“史实性”、“典雅性”、“深刻性”和“可读性”等。它的创作难度自然要比现当代题材的小说创作大得多。一部出色的历史小说精品,绝对是辛勤与智慧的结晶、阅历与文化的积淀、深刻与通俗交相辉映的产物。
我的《司马懿吃三国》小说共有万字,由凤凰出版社分为五大卷出版发行,其创作历程耗时长达10年之久。这长期的创作经验,也让我获得了一些创作历史小说的肤浅心得,愿意在此与大家分享,并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我个人认为,要写好一部历史小说,必须做到以下三点:
首先,写历史小说,务必要善于“写实”。对历史小说作品而言,各种历史细节描绘所呈现出来的真实是它永恒的魅力。历史小说家在他的作品中,献给读者的不仅是一场历史知识的通俗化普及,而更应该是一幅栩栩如生、真实可信的历史画卷与历史群雕去赏心悦目。当然,绝对纯粹的真实是做不到的。作家只能运用目前现有各个渠道所提供的有限的历史知识、资料和理论研究成果,进行艺术形象和社会生活的重构和创造,以使作品达到“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相统一”。这就是说,历史小说创作允许一定程度的虚构。但这种虚构必须建立在符合历史真实的合情合理的逻辑之上,而不是“戏说”、“穿越”之类的臆想。历史小说家,不可能让汉代的人在请客吃饭时用银两来结账,因为他们当时的“通用货币”是铢钱;也不可能让魏晋名士坐在板凳和椅子上清谈,因为他们当时的坐具主要是榻席;更不能让魏晋人物的口里突然冒出一两句李白、杜甫、苏轼的诗词,因为他们毕竟是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在这里,我要特别点出高希希导演的《新三国演义》。关于这部电视剧在“历史的真实性”上所犯的“漏洞百出”的谬误,我就不用去一一论述了。我只指出里面的一个“噱头”式的失实错误。《新三国演义》里把司马懿塑造成为一个披头散发、不修边幅、举止张扬的道士形象,这或许会在一定程度上吸引观众的眼球,但却是不符合历史真实性的。作为“服膺儒教”、胸有城府,谨遵礼法、注重外在形象的司马懿,怎么可能会以当时社会上并不占据主流意义的旁门道士的装束打扮来示人呢?他若敢不戴“进贤冠”、不穿正式的官袍出入官场,恐怕早被监察御史们攻击得体无完肤了!这反过来不正说明了《新三国演义》编剧的虚谬和肤浅吗?他以为三国时期的一代“谋略鬼才”司马懿就应该那么一举一动都透着异乎常人的姿态和张扬,殊不知在历史书籍中真实的司马懿却是“韬光养晦”、“重礼守法”、“谨小慎微”,装得比谁都更加中规中矩,决不授人以柄的。所以,历史小说的“写实”,一定要建立在真正读通相关历史的基础之上,而不能是异想天开、不合情理的主观臆造。在这方面刘和平的《大明王朝:嘉靖与海瑞》、二月河的《雍正王朝》就做得很好——每一个历史细节都透着符合“彼时彼境”的真实性。我们就是要善于用扎实的细节来还原、再现当时的历史情景,用一个个具体而准确的细节把历史人物塑造得合乎“彼时彼地”的现实,使读者有一种身临其境的现场感。这样的历史作品,才算是创作得比较成功的。
第二,就是要善于把历史人物“写活”。怎样写活?首先要让这个历史人物在历史的定位、定性上把握准确。曹丕肯定是狭隘之君,这从他打击曹洪、诛杀鲍勋等“逆我者亡”的言行完全可以体现出来,我们没有必要刻意为他“翻案”。应该在这一史实的基础上把他狭隘的个性表现写活就够了。对角色定位、定性准确之后,便要把这个人物的形像写得血肉丰满、个性鲜明、特色突出。这样,他才能“活”起来。“活”有两种形态:一是静态的“活”,用艺术的笔法把历史人物的外在形象、衣着风貌,写得立体可感,这是静态的“活”。二是动态的“活”,它体现在那个人物在那个历史情境下面对各种社会关系、各种现实事件错综复杂的作用下所做出的反应、表情、言谈、动作等。而这些反应、表情、言谈、动作都应该达到“恰如其分”、“恰到好处”的效果。这些书中的历史人物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表情、都应该适当地体现着他本身在历史场景中应有的阶层意识、身份意识、文化水准和能力水平。而且,也不能是仅仅表现在语言、动作、表情等方面的“活”,还要使他们的思想和灵魂也呈现出“活”的状态来。这样塑造出来的人物,才是“活灵活现”、可信可感的。我在这里举出我对司马懿这个人物塑造方面的有关理解来。司马懿的“活”,凸现在他非常复杂的个性特色上:一方面,他自幼“伏膺儒教”,在汉末战乱之际还不忘和兄弟们一道“研习典籍、披阅不倦”,是儒学义理和学说的忠实信徒;另一方面,他又用兵如神、法纪严明,是兵家、法家学术的集大成者。一方面,他胸中“常慨然有忧天下之心”,表现出一种难得的“铁肩担道义”的责任意识,对民众遭受的战乱困苦深有悲悯;另一方面,他“性深阻有若城府”,满腹的机诈诡计,对政敌是狠招迭出,令人防不胜防。可以这么说,司马懿的性格就是一个“多面体”。所以,要把他写活,就要把握住他个性深处的“常”与“变”、“本”与“末”。枭雄心性、胸怀大志,是他的“常”与“本”;而儒家面具、法家手段、兵家术略,则都是他的“变”与“末”。他所有的“变”都是围绕着他自己性格深处的“常”来铺开的。他所有的“末”也都是从他性格深处的“本”生发、延伸出来的。所以,他才能用自己的“儒家面具”去笼络士民之心,用“法家手段”去整合麾下各方势力,用“兵家术略”去击败对手,并最终达成他“肃清万里、独吞天下”的勃勃野心。也只有这样去描写,才会使司马懿这“一代儒枭”的形象立体化、丰满化、真实化,才会使他真正在书籍中“活”了起来。
第三,从历史小说的立意理念上要写“深”,做到洞明世事、入木三分。也许大家看我的小说第一个印象会是这里边各路英雄豪杰、能人贤士之间纵横捭阖、阴谋阳谋、明算暗算、斗智斗勇,实在是“好戏连台”、精彩迭出。但是,透过这些技巧性描写的背后,你会看到人性深处的阴暗与光明、狭隘与宽广、琐细与磊落的交替展现,也会发觉这会是作品中每个艺术人物自身特有的立身之道、待人之方、处世之术在碰撞和较量。再往里边更深一层去进行思索,你就会领悟到这《司马懿吃三国》的小说里铺开的这幅漫长的历史画卷当中,“如何善待于士”与“如何取信于民”这两个根本性问题才是主导三国时期每一个英雄名士成败得失的关键。曹操怒杀孔融,失了士心,所以在赤壁之战中孤掌难鸣,败下阵来;曹爽骄奢浮逸,丢了民心,所以在高平陵事变中自知大势已去,只得乖乖投降;孟达朝秦暮楚,反复无常,随时为了一己私利就出卖别人,所以到头来他也被自己的外甥和下属所出卖。这些情节,都透射着对三国历史人物各种得失经验的深刻反思与总结。反之,司马懿礼贤下士,任人唯贤,做到了“取邓艾于农琐,引州泰于行役,委以文武,名善其事”,这才实现了“百姓与能,大象始构”,奠定了三国归晋的坚实基础。这样的立意、这样的着笔,就让这部作品有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明得失之键”的深度,也就有了哲学经典一般的厚实与凝重。而这种深度和重量又不是通过空泛的说教和抽象的教条来呈现的,是巧妙蕴藏在一个个生动感人的故事当中的,这就不会让人读起来感到枯燥和晦涩,从而最大程度地获得阅读和思想交织作用的愉快。
“写实”、“写活”、“写深”,是写好历史小说的三个关键。我个人目前尚是才疏学浅,还必须与诸君不断在探索中共勉共进,共同为历史小说文苑的“百花齐放”一尽绵薄之力!
作者笔名:李浩白;
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忠县县委宣传部;
作者简介:重庆作家,年曾获“巴蜀青年文学奖入选奖”,出版有《司马懿吃三国》、《抗日援朝》、《盐战》等历史畅销书。